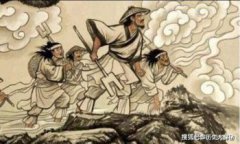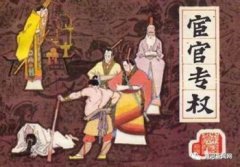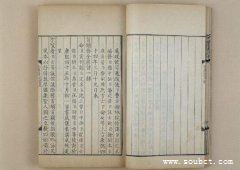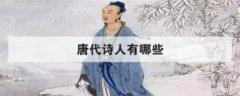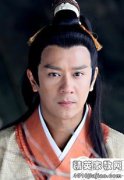實際上在一般人的印像之中,唐朝的文學類造就是十分高的,大家都會兒時念書期內背過唐詩三百首,而不是宋詩。但事實上,唐宋八大家中有六位全是宋代的作家,唐朝僅有倆位。很有可能很多人會怪異,為何詩仙李白和白居易等沒當選唐宋八大家呢?由于唐宋八大家是以短文為主導,并且她們全是實行古文運動的英模人物,那時候詩風興盛僅僅一個基本,真實把文學類造就提高一個級別的還是以唐宋八大家為代表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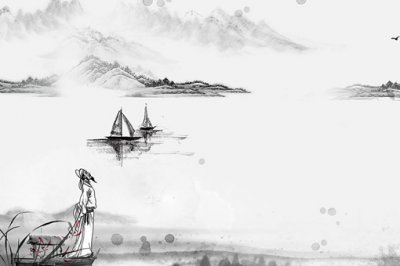
1.唐朝詩歌興盛
唐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文化藝術興盛的階段,在其中最舉世矚目的造就便是詩文,唐詩宋詞不但是中國古代歷史文化藝術的一顆燦爛耀眼明珠,也對全世界好幾個我國和中華民族的文化發展造成了危害。
唐詩宋詞在漢魏六朝樂府詩的基本上,不但拓展了五言、七言詩體方式的應用,還造就出了設計風格幽美齊整的近體詩裁,這對格律音韻擁有 嚴格管理的新詩體,將我國的詩文語言文化創意,推來到一個在歷史上完善的頂峰。
唐朝詩歌文化藝術的興盛,離不了唐朝成千上萬出色作家的著作,但為何我國左右數千年的歷史時間,唯有唐代的詩人引領風騷呢?這與唐朝的取士方式相關。
古時候的取士方式,從秦漢時期的“世官制”,到漢時的“察舉制”,再到先秦的“九品中正制”,至隋朝,“九品中正”的取士方式已不太合適執政的要求,因此隋文帝楊堅創新“分科舉考試人”,到楊廣階段,科舉考試取士規章制度宣布變成基本國情,隋滅后,唐代延用了隋的科舉制,并在隋的基本上開展了健全,以進士科為主,明經科其次。
“進士及第”是那時候知識分子較大 的榮譽,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寒窗苦讀十年,就僅僅為了更好地一朝“同榜”,一來能夠光耀門楣,二來一展心中理想或處理日常生活疲憊的難題,而唐代時,進士科關鍵考的便是詩賦,因此 唐朝科舉也是有“詩賦取士”之說。根據這一緣故,唐代詩風的風靡就不難理解了,如《資治通鑒·唐代宗廣德元年》中載:“考文者以聲病為是是非非。”“聲病”,便是詩文律動上的問題。因此 在唐朝,通常有眾多“相守窮詩”的知識分子,一生究詩研賦,只求考入個舉人,這倒讓許多優秀的詩歌作品,在這里荏苒的歲月里,被寫作了出去。
2.科舉考試功效極大
唐時的考舉人,比之明經科,難度系數但是為歷朝之最,因此 也是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舉人”的叫法,唐代的文學家韓愈,就曾一度不第,乃至連“詩圣“杜甫,在考時也是名落孫山,由此可見難度系數之高。除開倆位外,更有成千上萬學才出色的唐朝才俊競相落選,這也是為什么存留的唐詩宋詞作中多存抑郁之意的緣故了。
唐時科舉考試難考的難題關鍵還是源于科舉制上,唐代的科舉考試并沒有采用“糊名“制,士子考試前能夠公布舉薦,此謂“通榜”。而考舉人的士子,通常會將自身的著作遞呈給朝中有威望的人看,稱之為“溫卷”,像韓愈,在科舉考試期內就曾一度給丞相奏疏自我推薦,評委會依據學生的社會發展威望和才華做為取士時的參照。
那樣的科舉制,讓很多出生不太好,或知名度看不出的知識分子,科舉之路出現異常艱辛,如杜甫,盡管背后得到 偌大的知名度,但在那時候確是知名度不顯,因此 造成 官運不如意,一生貧困潦倒,連大兒子都被餓死了。而杜甫的詩作,盡管多發性憂國傷民之情,但內心深處釋放而出的,關鍵還是本身難展一身理想,以象收益我國的心而已。
3.描繪作家唐代切身體會
再如唐詩宋詞《己亥歲二首》的創作者曹松,一生研詩復習,卻無一中第,直至71歲大齡,遇上了皇上心情不錯,才下旨選拔任用一些出生窮困,報名參加過數次科舉考試沒有考中的學生,特賜“恩榜”,才最后變成了舉人。那時候同榜的五人群中有二人早已超出了七十歲,剩余的三人也都過去了六十歲,因此此次的發榜就被世人稱之為“五老榜”。
“五老榜”此謂那時候的美談,但事實上,這更像一種譏諷,曹松當初被授校書郎,后遷任秘書省正字,但這般風燭殘年,那堪疲勞,同榜第二年曹松便遠去。
曹松在唐朝成千上萬優秀的作家中知名度并算不上赫赫有名,但他在科舉考試道上荏苒一生所做的《己亥歲二首》,確是唐詩宋詞中的作品,如“憑君莫話封王事,一將功成萬骨枯。”也是名詩句。曹松一生都會科舉考試道上荏苒漂泊,因日常生活在最底層,也見多了貧苦老百姓的痛苦,再再加上屢考不第,心里當然免不了存在怨憤,“憑君莫話封王事”是譏諷那時候的寧波鎮海節度使高駢的詩句,高駢因前去鎮壓黃巢有功功率,封號渤海郡王,在曹松眼中,高駢之流不過是“功在行兇多”罷了,如同“一將功成萬骨枯”中深深地流露出來的厭煩和怨恨。
唐代的詩風因科舉考試而興盛,又因自然環境而轉變,因此 大唐盛世詩文多是斗志昂揚之作,而中晚唐詩文,由于戰爭和朝廷的腐壞,通常胸襟理想的有識之士,卻不可常用,一生漂泊艱辛,因此詩文的主要表現越來越沉穩沉寂,多有惱怒諷刺之作或顯出悲觀厭世隱居的心,如同唐代詩人韋莊,從“此生志業匡堯舜禹”,到之后的“又擬滄浪學釣翁。”它是大部分晚唐詩人政冶理想化毀滅后的切身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