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子算是朦朧派詩人,這個“幼稚”的詩人,有人曾不認為他的詩有何高超之處,即使曾以他的《面朝大海,春暖花開》模仿了兩首詩。有些專家甚至認為,他的詩歌只停留在中小學生水平上,他的詩像一個個童話故事。海子的好友西川曾說他“像一個赤子一樣的生活”,可見他不諳世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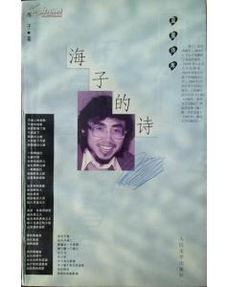
但敏感的他卻幻想寫出可以和歌德、但丁、莎士比亞比肩的史詩,最終留下《太陽-七部書》,沉浸于詩歌的園地,還自稱“王子”,也許他是一種無謂的自傲和脫離實際的自詡。就像現在的不少學生,有些字還懂不了幾個,卻沾沾自喜,稱其充滿童真童趣、幼稚可笑尚未成熟的“小說作文”美其名為“兒童文學”。
當然,海子還是比較有天賦的一員,15歲考上北京大學,19歲便分配到中國政法大學任教,有點類同法國的少年早熟的天才詩人蘭波,在同齡人中算是佼佼者。他曾與食指同獲第三屆人民文學獎詩歌獎,但他生前名聲不大,臥軌自殺后,名聲卻像滾雪球般逐漸壯大,響亮起來,以至于后來成為當代學院新詩人的代表。
難道是由于他在自殺兩個月前寫的《面朝大海,春暖花開》一詩中所體現出他是個理想主義者,對生活的態度應該是積極進取、樂觀向上的,而臥軌的最終緣由是完美的理想與不完美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到了不可協調的地步,因而要通過自殺來尋求解脫。
同時他在詩中所言的幸福其實是一種虛擬的幸福,讓人們產生誤解。在自身兩重人格彼此沖突時,無法自我解脫,最終造成悲劇。海子所謂幻想與渴望在《雨》、《五月的麥地》也同樣體現得出。他的文學宿命論便是他所言的“從明天起,做個幸福的人”。這種活在天堂便是幸福的奢望。在詩歌成就上,海子跟惠特曼、聶魯達一類詩人比起來,顯然是小巫見大巫。但是在中國當代詩壇上的地位,卻似乎不亞于其他著名詩人。我們讀詩,在于理解作者蘊含在詩中的意旨,也許海子這個矛盾的統一體是文學宿命論中的一個異數,才讓他開拓了一個詩的新領域,一個新時代。

















